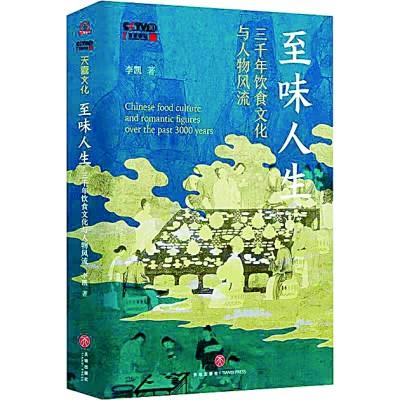
《至味人生》 李凱著 天地出版社

西園雅集圖(局部) 北宋李公麟繪選自《至味人生》
由食及史,這是研究飲食歷史的傳統(tǒng)范式。飲食的歷史融匯了生物醫(yī)藥、文學(xué)政治、社會(huì)生活、思想文化等多元學(xué)科的研究范疇。大量學(xué)者孜孜以求,在瑣細(xì)的研究中探尋食物的源起演進(jìn),以及飲食背后的政治結(jié)構(gòu)和歷史隱喻。但難處在于,素材如何形成邏輯鏈條,在素材和邏輯上“講”出故事,從而讓故事動(dòng)聽(tīng)而有意義?北京師范大學(xué)李凱的《至味人生:三千年飲食文化與人物風(fēng)流》(以下簡(jiǎn)稱(chēng)“《至味人生》”),就是“講”的嘗試。
《至味人生》一書(shū)脫胎于央視百家講壇“舌尖上的歷史”第二部講稿。一切歷史都是思想史,而思想史如何復(fù)盤(pán)就需要花心思。本書(shū)既沒(méi)有局限于以宏大敘事探討飲食流變,也沒(méi)有糾結(jié)于某一飲食元素的細(xì)枝末節(jié),而是進(jìn)行了一些敘述性的建構(gòu)。該書(shū)打破了就事論事的窠臼,發(fā)揮了歷史學(xué)“以小見(jiàn)大”“立地頂天”的優(yōu)勢(shì),把物質(zhì)文化與歷史演進(jìn)嵌合起來(lái)。14位名士是經(jīng)線(xiàn),他們的日常飲饌是緯線(xiàn),研究性敘事是血肉。借助“吃”,將千古名人、飲食、典籍、社會(huì)空間揉在一起,“講”出了中華文化的精神基因。
一幅立體的飲食畫(huà)面,要通過(guò)“人”的生活動(dòng)態(tài)予以呈現(xiàn)。“人”為天地之性最貴者,也是中國(guó)傳統(tǒng)史學(xué)敘事的第一要素,然而在“分析化”的現(xiàn)代史學(xué)中可能被人忽略。歷史學(xué)家并不是攝影師,而是畫(huà)家,對(duì)自然景象不是一一摘取,而是基于新異、審美、倫理、文化價(jià)值進(jìn)行遴選。這意味著“人”的現(xiàn)實(shí)淵源總是選擇內(nèi)容的標(biāo)準(zhǔn)。在“舌尖上的中國(guó)”火遍大江南北之后,關(guān)于“吃”的著作陡然增多,在古今飲食工藝流程上尋求看點(diǎn),已屬不易;那么從“吃”看“人”,從“人”看社會(huì)的思路就必不可少。并且,需要作者從大人物與常識(shí)入手,另辟蹊徑又不能故弄玄虛,才可能“新”而不“異”,從而易于大眾接受。作者抓住善于調(diào)和五味、將烹飪之技與治國(guó)之術(shù)融通的伊尹,以戰(zhàn)國(guó)策士的歷史背景與古史“層累”的思路來(lái)詮釋他;作者把“茶淫橘虐”的張岱、休閑文化的領(lǐng)軍人物李漁,以及能對(duì)廚師“執(zhí)弟子之禮”的大學(xué)者袁枚,放置在明清鼎革與新思想萌動(dòng)的背景下考察,很有歷史的厚重感。這些大人物也是“人”,更是歷史中的人,他們的行為活動(dòng)同樣是合目的性與合規(guī)律性的統(tǒng)一。正如作者所言,“把人當(dāng)作一切事物的中心,把人類(lèi)幸福當(dāng)作一切知識(shí)的終結(jié),于是強(qiáng)調(diào)生活的藝術(shù)就是極為自然的事情了。”
作者對(duì)飲食背后的細(xì)節(jié)作了窄而深的叩問(wèn),這是書(shū)中引人入勝之處。作者結(jié)合《楚辭》等文獻(xiàn)、戰(zhàn)國(guó)帛畫(huà)等圖像史料和馬王堆相關(guān)考古資料,向讀者生動(dòng)呈現(xiàn)了屈原形象的另一面:瘦骨嶙峋、“朝飲木蘭之墜露兮,夕餐秋菊之落英”的同時(shí),也同樣愛(ài)“肉”,諳于鐘鳴鼎食的生活。這符合他楚國(guó)貴族的身份,與他追求高潔的精神氣質(zhì)并不矛盾,后者正是對(duì)前者的超越。作者抓住了大文豪蘇軾《晚香堂蘇帖》中的《獻(xiàn)蠔帖》,從文獻(xiàn)的字里行間追尋蘇軾在“食無(wú)肉、病無(wú)藥、居無(wú)室、出無(wú)友、冬無(wú)碳、夏無(wú)寒泉”的天涯海角白手起家、苦中作樂(lè)的生活經(jīng)歷和天真爛漫、百折不撓的精神面貌。尤其作者陳述蘇軾在海南栽培青年俊秀姜唐佐,留下“滄海何曾斷地脈,白袍端合破天荒”的典故;詩(shī)句直到姜唐佐及第以后由蘇轍補(bǔ)全,其時(shí)蘇軾已然作古。令讀者感慨的同時(shí),蘇軾的忠純和偉岸在滄桑中凸現(xiàn)出來(lái)。作者敘述蔡京把宋徽宗的盛宴上升到理論高度:“豐亨豫大”——不盡情享受,那是違背天意;靖康之變后徽宗皇帝淪為囚虜,不禁發(fā)出“玉京曾記舊繁華,萬(wàn)里帝王家”“家山何處,忍聽(tīng)羌笛,吹徹梅?花”的怨語(yǔ)。前后反差,不勝唏噓。
作者的研究性敘事是有趣的。一方面,他引用了大量官私史書(shū)、筆記、小說(shuō)、文集等傳統(tǒng)史料,善于利用甲骨文、簡(jiǎn)牘以及考古報(bào)告等一手史料,考訂翔實(shí)、論證充足;另一方面,作者重視前輩專(zhuān)家的研究成果,引用了顧頡剛、章太炎、梁?jiǎn)⒊⑾蜻_(dá)、陳寅恪、晁福林等學(xué)人的觀點(diǎn)并進(jìn)行論述,以學(xué)術(shù)講人生,言簡(jiǎn)意賅。比如針對(duì)《關(guān)雎》中青年男女的身份背景、誰(shuí)是第一個(gè)吃螃蟹的人、發(fā)明豆腐的人是不是劉安等大眾感興趣的話(huà)題,作者的闡發(fā)就有深度。此外,作者還有一定的中醫(yī)理論與醫(yī)療知識(shí)儲(chǔ)備。比如,基于“食醫(yī)相通”敘述古人的養(yǎng)生知識(shí),論及若干食材與經(jīng)方的臨床價(jià)值等,這些內(nèi)容都呈現(xiàn)出作者的知識(shí)結(jié)構(gòu),構(gòu)成了“有意義的細(xì)節(jié)”。英國(guó)史學(xué)家奈米爾認(rèn)為,歷史最重要的是有大綱領(lǐng),兼具有意義的細(xì)節(jié);必須避免的,是無(wú)謂的敘事。基于此,有學(xué)者指出不作無(wú)謂的敘事,只有在敘事與解釋冶于一爐時(shí),才大致能做到;歷史不流于年鑒或斷爛朝報(bào),胥系于此。作者把敘事和解釋融合得較為自然,名士、飲饌和研究性敘事交錯(cuò)在一起,解釋引領(lǐng)敘事,敘事輔助解釋?zhuān)泄侨庀噙B之意。如作者敘述“老饕”張岱在明亡之后的遺民之恨,引其《自為墓志銘》“破床碎幾,折鼎病琴,與殘書(shū)數(shù)帙,缺硯一方”之言,與先前鐘鳴鼎食、酒醉飯飽、書(shū)蠹詩(shī)魔的狀況如同天壤。這是張岱晚年的敘述,又何嘗不是對(duì)先前“茶淫橘虐”的詮釋呢?這樣讀者自然體會(huì)到士大夫奢侈精致,不過(guò)是特定歷史時(shí)空的產(chǎn)物罷了。在詮釋過(guò)程中作者善于把握歷史側(cè)影背后的大環(huán)境、總原因和發(fā)展軌跡。誠(chéng)如晁福林先生所言,從大處著眼,不拘泥于碎片,對(duì)歷史教育的意義是不可小覷的。
歷史的教育價(jià)值在于明理。飲食除了滿(mǎn)足個(gè)體口腹之欲之外,還存在更為豐富復(fù)雜的生命體驗(yàn),尤其是超乎經(jīng)驗(yàn)的人生哲理。其中政治史是歷史敘述的主干,作者特別留意。該書(shū)看到了作為美食家的宋徽宗對(duì)中國(guó)傳統(tǒng)宴會(huì)制度的創(chuàng)新發(fā)展所作出的貢獻(xiàn),又自然而然地揭示出盛宴背后的宋王朝的危機(jī),從而原始察終、見(jiàn)盛觀衰。作者講述曹操釀酒的故事,突出他和漢獻(xiàn)帝之間千絲萬(wàn)縷的聯(lián)系,讀者能體會(huì)到即使是叱咤風(fēng)云的大人物也需要“借勢(shì)”。該書(shū)著眼于漢族和少數(shù)民族之間的文化交往,剖析《洞冥記》中善苑國(guó)供奉給漢武帝螃蟹故事的真真假假,解讀出中原和西域各族的經(jīng)濟(jì)文化往來(lái);聚焦于《齊民要術(shù)》和《本草綱目》的西域農(nóng)作物,折射出漢家文化的恢宏氣度。書(shū)中講述唐玄宗與胡餅、羊肉、胡酒的故事,試圖揭示盛唐時(shí)期胡漢一家的文化盛況,呈現(xiàn)出唐王朝的多元文化構(gòu)成以及中華文化海納百川、兼容并包的精神氣度。作者在社會(huì)“大歷史”下討論人物的“小歷史”,如借助飲食、結(jié)合中晚唐時(shí)期的動(dòng)蕩政局講述杜甫的萍蹤浪跡,揭示“大歷史”中的人物命運(yùn)沉浮。唐玄宗在“漁陽(yáng)鼙鼓動(dòng)地來(lái)”之后,拿到胡餅也狼吐虎咽,徑直逃難到蜀中;宋徽宗被俘虜?shù)奖眹?guó)時(shí),看到包裹“茴香”的紙張居然是兒子趙構(gòu)登基的文誥,不禁喜極而泣,感慨道:“夫茴香者,回鄉(xiāng)也,豈非天乎?”這說(shuō)明,即使是貴為天子的唐玄宗、宋徽宗,在兵燹中也照樣倉(cāng)皇狼狽,此時(shí)個(gè)體生命如此渺小,帶有很強(qiáng)的歷史唯物主義色彩。
突出中華文化的合理性,為現(xiàn)代中國(guó)人尋求精神家園,是本書(shū)的出彩之處。書(shū)中著重介紹豆腐,從淮南王劉安的求仙偶得,到尋常百姓的盤(pán)中餐,蘊(yùn)含著王謝堂前燕的滄桑,也流露出古人巧妙地利用自然、在實(shí)踐中尋求食材的智慧。作者勾勒出古人豐富多元的交流空間,如以江南文人張岱為代表的晚明縉紳,把美食和文人生活融合,催生出了茶會(huì)、蟹會(huì)等飲食空間,形成了一種獨(dú)特的精致生活方式,不僅“融合了不同地域的社會(huì)風(fēng)俗,引領(lǐng)著社會(huì)各階層的生活風(fēng)尚,也潛移默化地改變著市民階層的生活情趣”。可見(jiàn),“王道本乎人情”“穿衣吃飯即是人倫物理”,也是中國(guó)古代士大夫文化的一種別致的樣態(tài)。在“吃”的敘述過(guò)程中,讀者不難發(fā)現(xiàn)字里行間深厚的中華文化認(rèn)同。
《莊子》說(shuō):“道不欲雜”。為了提高可讀性,作者在書(shū)寫(xiě)過(guò)程中盡量脫去晦澀難懂、理論艱深的學(xué)術(shù)論述,在敘事風(fēng)格、語(yǔ)言習(xí)慣和圖文呈現(xiàn)方式等方面,力求干凈簡(jiǎn)潔,有干貨、有思想,但不故弄玄虛、故作深刻。作者以“孟子不信邪”“有好吃的,回來(lái)吧”“不死藥的烏龍”“不‘遠(yuǎn)庖廚’的曹操”等小標(biāo)題,采用詼諧俏皮的方式來(lái)點(diǎn)題。該書(shū)回避了晦澀的古代禮俗制度的闡釋與考證,盡可能講述歷史故事浸潤(rùn)倫理、審美和價(jià)值;以研究性的敘事方式,深入淺出地傳達(dá)了學(xué)術(shù)信息;反復(fù)打磨史料譯文,用通俗易懂的詞語(yǔ)拉近與讀者之間的距離,兼顧了趣味性和學(xué)術(shù)性。
作者:劉惠,天津理工大學(xué)馬克思主義學(xué)院副教授